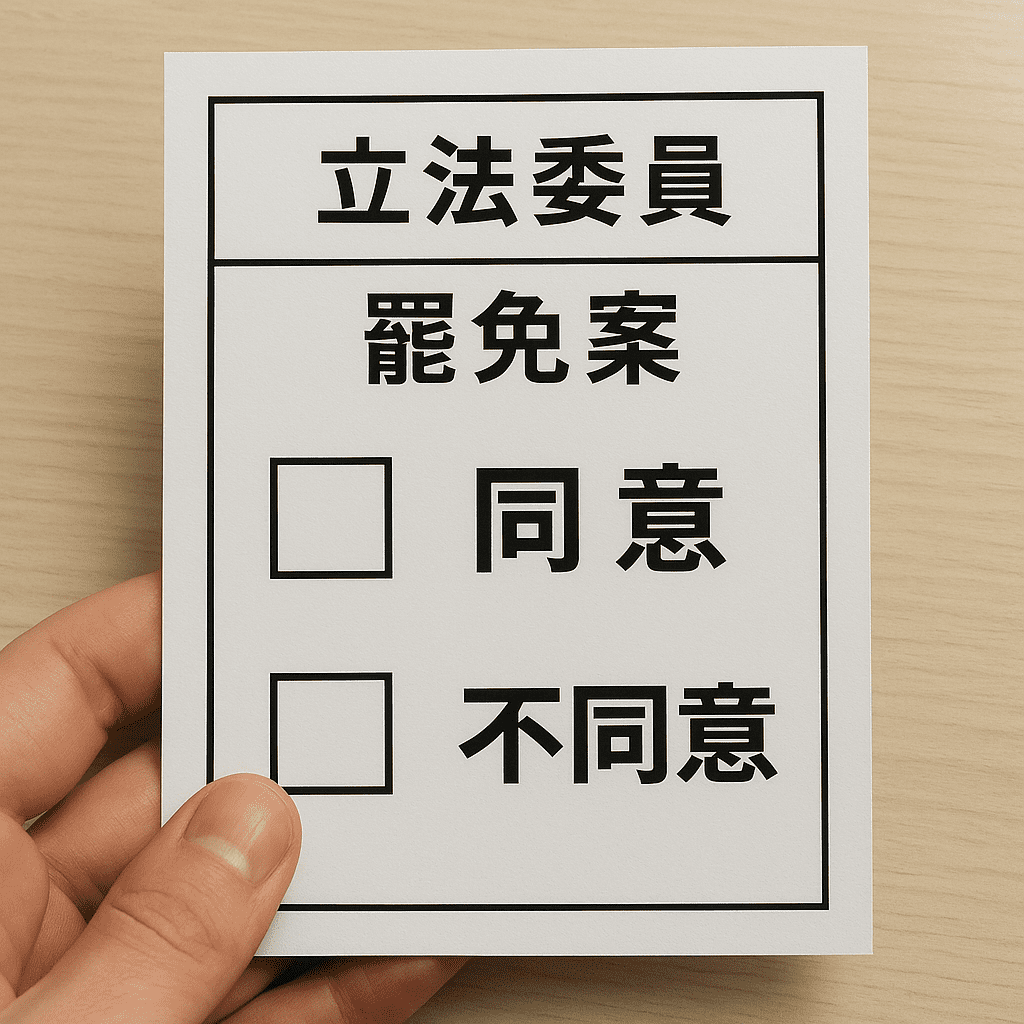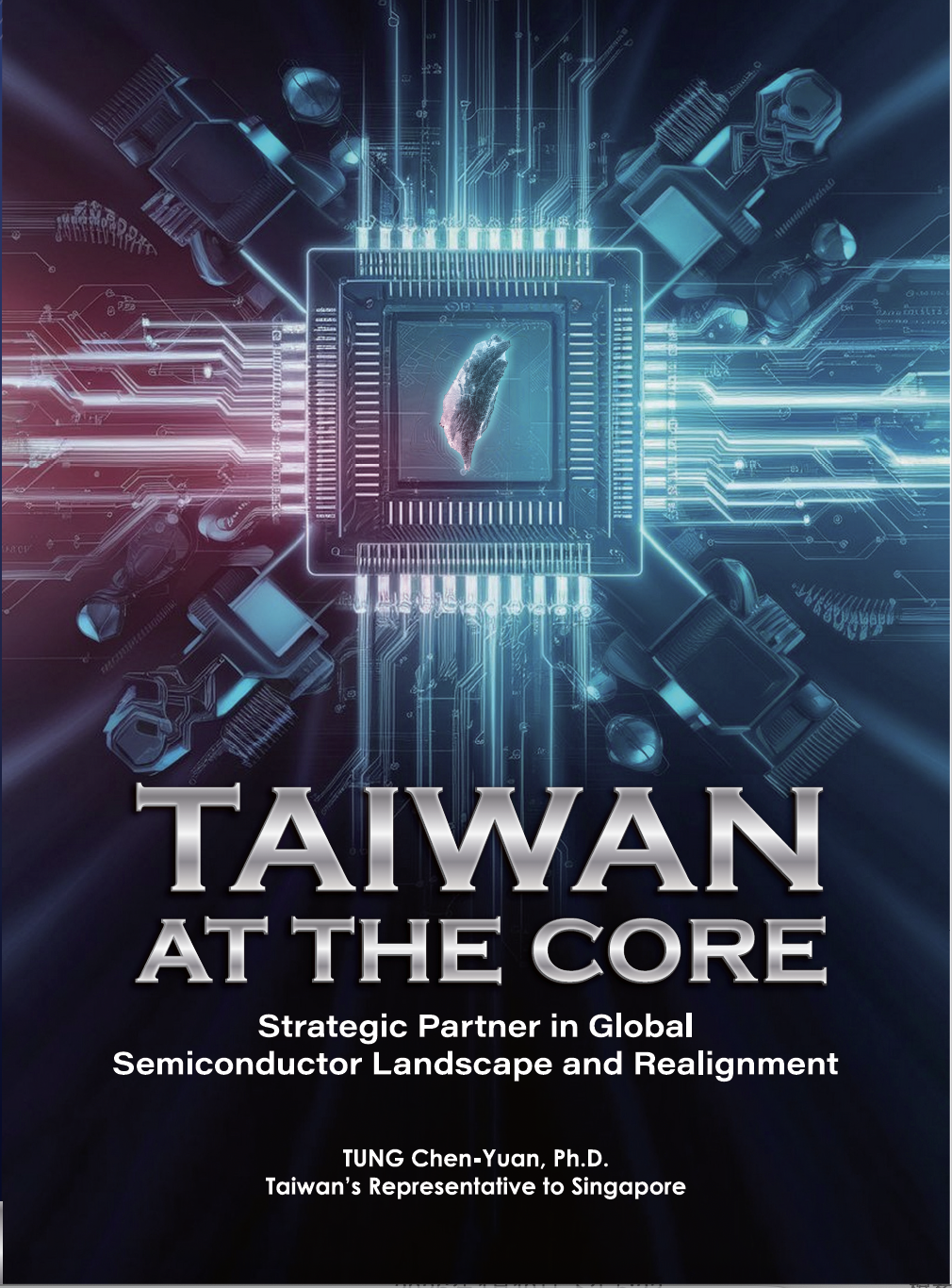大罷免投票將在週末展開,但大罷免的結局已經註定,桃園六席國民黨立委將全數過關,促成這個結果的關鍵是:罷免二階段後,民進黨未站在第一線整合支持罷免力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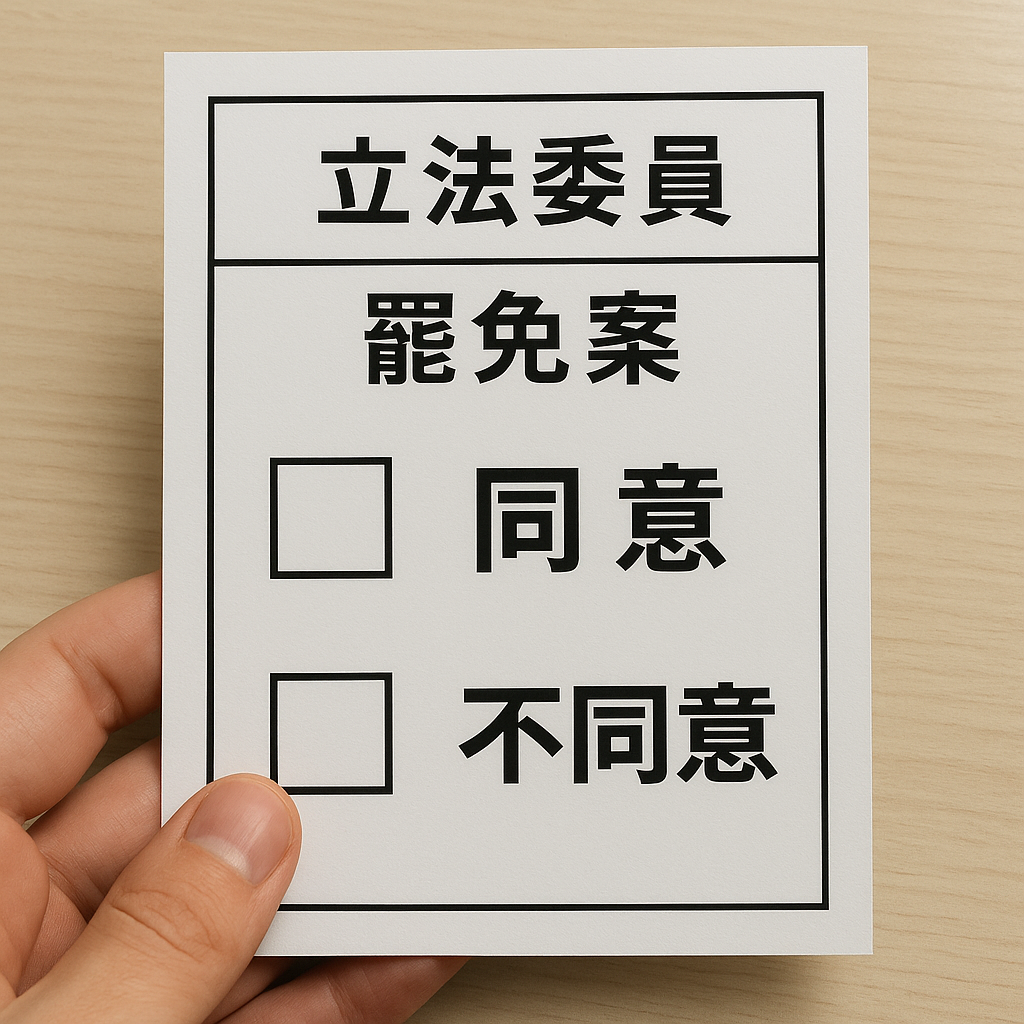
這場罷免本應是一場釐清國家認同與掃除地方黑金勢力之戰,卻因民進黨對戰略目標模糊、戰術執行軟弱,讓這場原本可贏的罷免選戰淪為全盤皆輸。桃園原是搖擺區,任何一席立委的動搖都可能引發連鎖效應,結果卻是國民黨席次穩如泰山,反而激勵其基層系統更加穩固。民進黨不只錯失良機,更讓對方擴大戰果,民進黨則在結構性鬥爭中被動挨打,最終自毀聲勢與士氣。
民進黨最大戰略錯誤,是未能掌握此次罷免案的核心主軸──對外有「國家認同的危機」,對內有黑金問題。
當一群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,卻集體赴中國與高層官員會面,回台後推動一連串有利對岸的法案,這樣的行徑已讓他們不再適任。這不只是政黨之爭,而是對憲政體制與主權的背叛。民進黨若能強調「罷免喪失國家立場的立委是捍衛民主根本」,將爭點推向安全與體制的高度,局勢早已改觀。然而他們卻將「認知作戰」限縮為媒體話術與資訊真假,忽略背後深層的認同混淆,錯失升高戰場的絕佳時機。
戰略模糊導致情感動員貧弱。此次大罷免無法如同2014年太陽花學運激起反黑箱的怒火,也未重現2024年青鳥行動的亡國焦慮。民進黨不但未喚起群眾共同記憶,甚至連一場能讓年輕人集結的象徵性行動都拿不出來。在社群平台與街頭聲量皆低迷的情況下,罷免案變成冷感操作,失去了最寶貴的民意勢能。年輕世代不再像當年為了服貿協議奮起,這場選戰的「危機敘事」幾乎不存在,民進黨只能眼睜睜看著選票流失。
更令人痛心的是,在戰略目標失焦之下,本該優先清除的立委反而逃過檢驗。以牛煦庭為例,其言行長期站在台灣主體性與民主防線的對立面,卻始終未被作為罷免首要對象。民進黨未能升高國家認同的論述戰場,也無意明確點名,使得他成功避開風暴核心。最終牛煦庭不僅未被鎖定打擊,還藉由國民黨的組織動員穩住地盤,搖身一變成為罷免風暴中的倖存者,這不僅荒謬,更反映民進黨完全失去戰場主導權。
民進黨在戰術層面同樣錯亂,錯失了一舉掃除地方家族壟斷政治的機會。
以呂玉玲為例,她的政治資源與組織力量長年盤據地方,以家庭為核心,盤據地方、建立派系根基,順利進入國會,兒子也接棒擔任議員,形成完整的家族接力體系。這類以家庭為單位壟斷地方民代席次的政治型態,正是台灣政治長期難解的沉痾,卻未在此次罷免戰中受到檢視。
呂玉玲之所以能穩坐選區,不是因為政績特出,而是透過地方組織密布、長期經營社群關係,打造出高黏著度的穩定選民結構。民進黨若真有意挑戰地方派系的既得利益體系,本應將這類政治勢力作為罷免戰的主要論述;但如今淪落政黨惡鬥,結果不但失衡,也讓根本問題被掩蓋。民進黨曾動員青鳥集結高喊清除黑金,如今卻放任老派勢力續留國會,錯過一次結構翻轉的歷史契機。
國民黨的成功不在於選民偏好,而在於動員戰全面啟動。他們把這場罷免戰當作存亡之戰,展開從村里長到社團宮廟的全面動員。像牛煦庭這類原以空戰見長的立委,也迅速補強地面網絡,建構屬於自己的地方系統,實現陸空合擊的選戰格局。反觀民進黨,全黨未發動總動員,地方系統失聯,中央僅象徵性表態。投票日當天,藍營投票率極可能超越常態選舉,綠營支持者卻普遍冷淡,這場投票率的懸殊直接奠定了罷免的潰敗結局。
罷免進入第三階段後,選戰已從倡議轉為攻防,理應是政黨接手整合戰線的關鍵時刻。然而民進黨卻選擇觀望,未能積極介入,也未提供策略與資源協助公民力量轉化為實質動員。大量熱情參與的基層志工與公民團體,最終如散兵游勇般各自為政,缺乏節奏、缺乏支援,更缺乏一個能統合全局的號召平台。這不只是戰術延誤,更是組織意志的潰散,使罷免能量在臨門一腳時徹底熄火,錯過了可能改變歷史的關鍵機會。
值得澄清的是,大罷免絕非政黨惡鬥,更不是民進黨的鬥爭工具。罷免權明載於《憲法》與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,是民主制度賦予人民的正常機制,用以淘汰不適任的民選代表。即使反對者對其批評,仍無法否定其制度正當性。相較之下,幽靈連署、違憲擴編預算的惡法修正,才是真正危害體制的行為。將罷免污名化為惡鬥,不但混淆視聽,更矮化台灣民主制度的自我防衛能力。
面對這次罷免的潰敗,不能僅看作戰術挫敗,而是民進黨在國家認同與地方治理兩條戰線同時潰退的警訊。民意不是天然的,也不會永遠站在民進黨這邊。當民進黨不敢升高戰場、也無力揭露對手的結構性問題,只會讓人民逐漸失去信任。桃園六席全數過關,只是這場潰敗的象徵。若不正視這次失利背後的深層根源,未來在2026與2028,民進黨恐怕將失去的不只是選票,更可能失去重新定義台灣政治未來的主導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