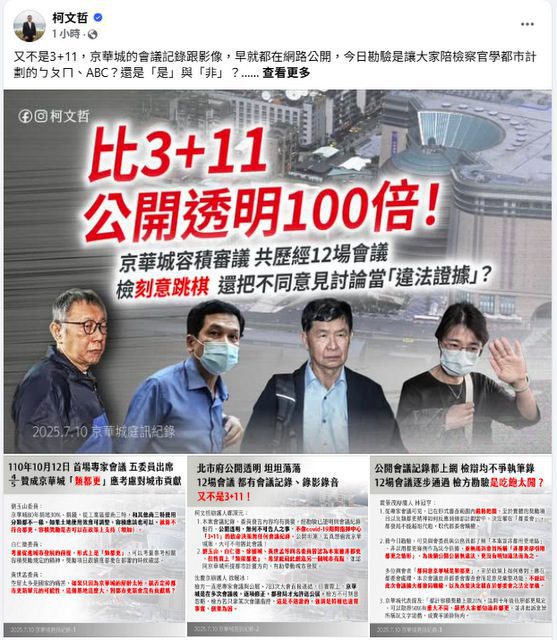(焦點時報/鄒志中報導) 在京華城案的法庭上,前台北市都發局長張景森的一句話——「我的專業不容許我再沉默!」——在政治與輿論的交錯裡,顯得異常刺耳。這句話應該不是在為柯文哲辯護,而是一種體制內官員對行政良知的最後防線。當司法與政治糾纏不清,「圖利罪」這個模糊的法律邊界,正成為壓在公務體系上的無形「緊箍咒」。
張景森的證詞被解讀為「對柯有利」,但他關心的焦點並非個人政治命運,而是「依法行政」能否還夠在「恐懼」與「懷疑」中存活嗎?這絕對不只是一起官司的問題,而是整個行政體系的危機:當專業被政治化,當誠實的陳述被視為「選邊站」,公務員又該如何自處?

專業倫理與政治解讀的斷裂
張景森有近30年的公職經驗,橫跨土地、都市計畫與建設…等高風險的領域。他是最了解「圖利罪」的模糊地帶:在都市計畫、土地變更、開發審議…等的決策中,幾乎每一個「選擇」都可能被「事後檢視」與解讀為「圖利特定人」。他指出,檢方引用的「法條」大多屬於「行政指導」,根本並非「刑法」中可構成「違法」的「法令」。
在這樣的區分中,對「法律」與「行政」而言,這是最基本常識;但在「政治語言」中,它卻容易被曲解為「卸責」或是在「包庇」。在輿論的二元對立中,「依法行政」與「圖利罪」常被混為一談。這正是他無法再保持「沉默」的原因——因為「專業」若不能狗被「法令」所捍衛,政策與城市治理就會淪為「政治鬥爭」的犧牲品。

當「圖利罪」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
「圖利罪」原意是防止官員濫用職權謀取不當利益,但在台灣的政治實踐中,它逐漸演變為「政爭」的武器。政治人物、媒體乃至社群輿論,都能輕易以「圖利」之名攻擊異己。這樣的結果是什麼?絕對不是讓台灣擁有更乾淨的政府,而是更畏縮與無所事從的行政體系。
正如張景森所言:「讓行政官員人人自危,無法依法行政,陷入僵屍狀態,只有領薪水時是活的,其餘是死的…。」這句話令人不安。當公務員害怕「做錯」,寧可「不作」時,當「依法行政」變成「避事求生」,整個國家治理能力就要開始變成退化。
美國經濟學者赫許曼(Albert Hirschman)曾指出,組織衰敗往往不是因為腐敗,而是因為「聲音的消失」——當內部成員不再說真話,只剩下「服從」與「沉默」。台灣行政的現場,正在逐接近這種危險的困境。
政治的「良知」與「方便」
張景森直言,自己從未考慮「證詞」最後會對誰有利。他的出發點,只是在「陳述事實」,而非考量「個人得失」。「如果因為他說的話對柯文哲有利就不說,對他不利就誇大,那就是對良知的背叛。」這句話的弦外之音,是對台灣整個政治文化的控訴。
在台灣,「對誰有利」往往比「是非對錯」更重要。媒體問的不是「事實是什麼」,而是「這樣會不會影響選情」。政治人物則精於操作輿論,把司法過程轉化為輿論戰場。結果,「真相」被邊緣化,「正義」被娛樂化,「專業」被政治化。
這樣的現象,其實在許多民主國家也出現過。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(Lawrence Summers)曾說:「我第一次為我的國家感到羞恥!」,在政治勢力干預專業決策、使公共政策淪為權力工具時,這句話放在今日的台灣,仍然讓人非常不安。
公務倫理的系統性危機
張景森不是第一個為「專業」發聲的官員,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近年從防疫政策到都市計畫,許多公務員在政治壓力下都紛紛選擇「沉默」。這不僅是個人抉擇的問題,而是一種系統性病徵——當政治與司法的界線模糊,當輿論懲罰「說真話」的人,台灣整個官場制度將逐步喪失自我修復的能力。
這種現象可以用經濟學的「道德風險」解釋:當行為者知道「誠實」會帶來「懲罰」、「沉默」反而安全,就會選擇「沉默」。長期下來,就會導致行政效率下降,決策品質惡化,公共建設停滯不前。最終,受害的不是政治人物,而是整個台灣社會。
從個案到結構:誰在傷害依法行政
京華城案表面上是一宗都市更案的爭議,但更深層的意義在於,社會如何看待「行政裁量」。台灣社會長期傾向以「結果」判斷行政作為,一旦開發案引發爭議,官員們立刻就會被懷疑是在「圖利」;但若決策遲緩,則又會被指責為「怠惰」。
這種兩難環境下,公務員自然趨於保守。沒人願意成為第二個「被法辦」的官員。這種恐懼效應,使得「依法行政」變成一句空話。沒有明確的行政法規範圍、沒有保護誠實官員的制度,再多的政治口號,也難以挽回信任。
政治競爭與制度文化的轉型
在貼文最後,張景森呼籲朝野應學會「尊重對手」,拒絕「暗黑部隊」與「網軍政治」。這絕對不只是道德呼籲,更是一種制度建言。當「政治競爭」淪為仇恨遊戲,專業被摧毀,社會分裂也將再無法被彌合。
事實上,制度成熟的國家往往建立在「尊重程序」之上,而非「懲罰對手」之上。日本、德國等國在行政法體系中明確界定裁量範圍,保障公務員「依法行事」的空間,因此也就能夠維持政策的穩定與投資的信心。台灣若想走向「成熟民主」,就必須從改革「圖利罪」的模糊地帶開始做起。
長期觀點:從恐懼治理走向信任治理
短期看,張景森的證詞或許影響京華城案官司最後的判決;但長期看,他挑戰的是台灣整個行政文化的恐懼結構。當專業的聲音被壓制、良知被懷疑,台灣的民主就會在「沉默」中瓦解與支離破碎。
行政體系需要的不是更多的「問責口號」,而是更清晰的制度邊界與對誠實官員的保護。只有當依法行政的官員敢於說出這就是「依法行政」,而不必再擔心被貼上「政治標籤」,台灣的「法治社會」才算真正成熟。
或許,張景森並不想成為任何政治人物的辯護者。他只是在提醒社會:在民主政治裡,最危險的不是「說錯話的人」,而是「再也不願說話的人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