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(焦點時報/鄒志中報導) 「在法定人數不足的前提下,憲法法庭自始不具備審判權(Jurisdiction)。因此,僅由五名大法官署名的判決,在法律上必然無效!」立法院藍白陣營於去年12月20日合力通過《憲法訴訟法》修正案,拉高大法官評決門檻。憲法法庭竟然在日前還做出「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」,由於憲法法庭未依法組成,自始不具審判權,只由5名大法官作成的判決應為「無效」? 對於憲法法庭無法正常運作的現實困境,根源在於大法官缺額的事實,根本解決之道在於依憲法程序補足大法官缺額。。
日前公布的「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」,表面上是對《憲法訴訟法》部分條文的合憲性審查,但從憲政結構的高度審視,此案引發的核心危機,並非法律解釋的差異,而是憲法法庭是否擁有超越法律約束、自行決定其合法成立條件的權力?
這起事件的實質是:一個在法定人數上未能成立的憲法法庭,仍然行使了終局裁判權,並且以「宣告違憲」的方式,清除了限制其成立的法律障礙。這構成對立法權的實質凌駕,對台灣法治底線投下巨大陰影。
法治危機:否定法律對自身的組織拘束力
三位大法官(蔡宗珍、楊惠欽、朱富美)在不同意見書中,提出了極為尖銳且無法迴避的核心質疑:
「在法定人數不足的前提下,憲法法庭自始不具備審判權(Jurisdiction)。因此,由五名大法官署名的判決,在法律上必然無效。」
這不僅是對判決結果的反對,更是對程序合法性的根本挑戰。法治的基本原則要求,任何權力行使者,包括最高司法機關,必須先滿足法律賦予其存在的先決條件。如果法庭可以自行認定其存在,那麼它否定的,正是法律對其自身的組織性拘束力。
法律與現實的巨大鴻溝:法庭成立的明文要件
《憲法訴訟法》是經過立法院三讀、總統公布生效,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。其中對「憲法法庭」成立的門檻規定得極為清楚:
1. 參與人數門檻: 「憲法法庭」作成判決,至少須有 10 名大法官參與審理。
2. 同意人數門檻: 「憲法法庭」作出違憲宣告時,至少須有 9 名大法官同意。
然而,本案在進行審理時,實際在任的大法官僅有 8 人。
在任何一個堅守法治原則的國家,面對這種狀況,結論只能有一個:「憲法法庭」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成立要件,即無法做出任何有效的終局判決。「憲法法庭」沒有「先審再說」的特權,更不能享有「自我例外」的憲政地位。
多數意見的實質邏輯:排除障礙以達成目的
「憲法法庭」日前宣告《憲法訴訟法》相關條文違憲,其論證邏輯儘管包裝了程序正義與權力分立原則,但其核心的實質路徑卻是:
1. 法律設定了阻礙: 法律規定「憲法法庭」的高門檻(10人參與、9人同意)使目前(8人)的法庭無法合法開庭審理。
2. 目的優先於程序: 「憲法法庭」為了能夠審理案件、行使職權,必須移除這個障礙。
3. 自我賦權行動: 因此,「憲法法庭」宣告限制自身的法律條文違憲,從而解除對自身權力的拘束。
這種行為在憲政理論上,被稱為權力的自我授權(Self-Authorization),其危險性在於,它使一個被授予的權力機構,得以繞過授予者(立法機關),自行擴張或變更其權限範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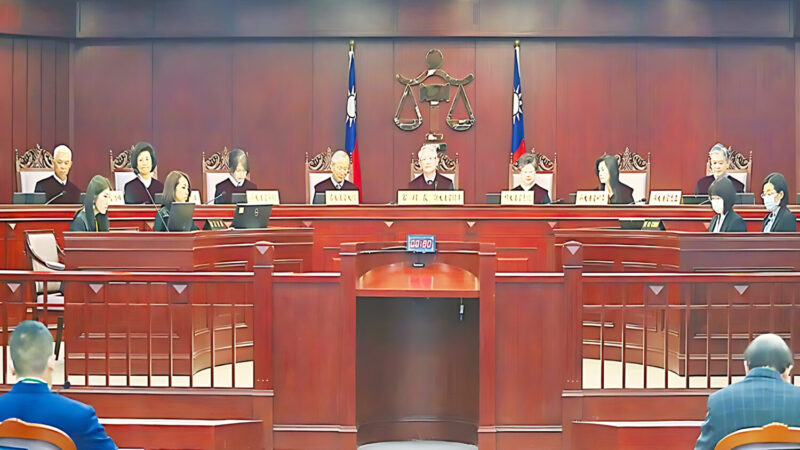
憲政警訊:凌駕而非解釋,決斷而非權衡
「憲法法庭」過去亦曾面對人數不足或政治僵局,但從未如此徹底地跨越這條紅線。本案的特殊性在於:
無視生效法律: 在明知不符合法定人數門檻,且法律仍有效的情況下。
未採取合法例外機制:未尋求任何合法的、體制內的解方(如類推適用例外規定)。
直接做出「立即失效」的違憲宣告。
這已不是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尋求解釋或權衡,而是以司法決斷的形式,明確凌駕於立法機關制定的組織法律之上。
制度後果:當權力最終裁量者不受制約
真正令人擔憂的,並非單一判決的內容,而是此例所確立的制度性後果。一旦此邏輯被接受,將為未來的「憲法法庭」開啟一道危險的權力之門:
如果因人力不足,可以自行降低成立門檻;
如果法律不方便行使權力,可以先宣告其違憲;
如果案件急迫,可以先審判、再補正程序。
在這樣的體系下,法律對「憲法法庭」的拘束力將形同虛設。「憲法法庭」將不再是憲法的「守門人」,而成為自身權力範圍的最終裁量者。這嚴重掏空了「依法審判」的程序意義。
權力上收:以權力分立之名,解除自身枷鎖
本案的論述存在巨大的反諷:多數意見高舉「權力分立」的大旗,主張立法院修法干預了司法權,但實際達成的效果卻是權力上收:
1. 立法權被否定: 立法院依法三讀通過的組織性法律被宣告無效。
2. 行政權被架空: 總統依法公布的法律被否定。
3. 司法權的自我鬆綁: 「憲法法庭」自身不符法律要件,卻反而取得了最終的裁量權力。
當「憲法法庭」以「防止他權干預」為名,解除法律對自身的組織性限制時,這已非憲政平衡,而是一種憲政例外狀態的展現。
法律體系內的備選方案被選擇性忽視
值得強調的是,三位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並非主張憲政僵局。她們明確指出了一條在現行法律體系內可行的、更具正當性的解決方案:
類推適用《憲法訴訟法》第30條第5項: 該條文規定在特殊急迫案件下,可由全體在任大法官參與,並經四分之三以上同意作為例外處理。
這顯示:憲政體系並非無解,而是多數意見選擇了風險最高、約束最少的一條路徑。 在憲政體系中,對於解決路徑的選擇本身,就是一種重大的價值判斷。

誰來限制「最後的限制者」?
「憲法法庭」作為體制內的最後防線,其合法性應當是所有權力中最不容質疑的。然而,正因其地位無可取代,它更不能成為第一個拒絕受制於法律的權力機構。
這起事件迫使台灣社會正視一個系統性問題:當「憲法法庭」自己可以決定自身的合法存在與組織門檻時,台灣的法治體系還剩下什麼外部制衡機制?
「憲法法庭」這場爭議無關藍綠或政治立場,其核心在於:台灣是否仍存在任何法律,能夠真正約束最高司法權力本身?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,那麼失去效力的,將不只是《憲法訴訟法》的特定條文,而是支撐台灣民主運作的「依法而治」這項根本原則。










